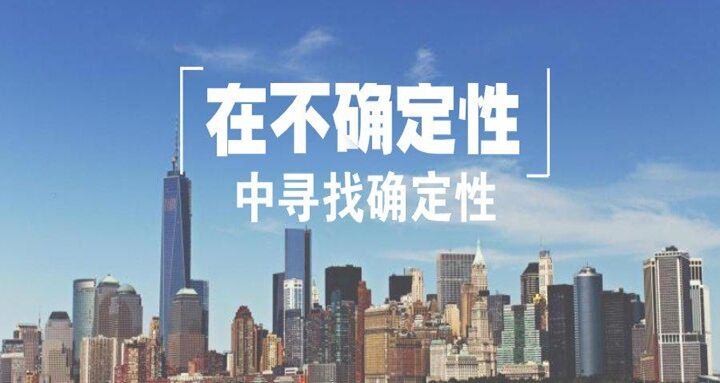您的位置:资讯>观察>顺风车规范化还需要迈过哪些“坎”?
即使是一场仅有少数研究者参与的会议,在顺风车的诸多事项――顺风车认定、平台角色、监管方、定价等――上也尚未能完全达成一致。
3月16日,城市智行研究院主办了一场名为“顺风车健康发展”的座谈会,按照会议方设置的议题,首当其冲被讨论的是顺风车本质特征,
尽管国务院2016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58号文)对于从原则上对顺风车进行了定义――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但是在实践中的认定仍存在一些讨论的空间。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委员会委员刘汝忠认为,顺风车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两点,一个是非营利,即所有顺风车应该是一种合理分摊成本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赚钱;二是非运营的,即车主应该以自我出行为前提条件。
延续这一思路需要考虑的三个问题在于:顺风车该如何定价?顺风车是否应该有次数限制?一次顺风车行为的达成形式应该是怎样的?
鉴于顺风车非营利的特征,大部分专家持有应该对顺风车的价格进行明确限制的观点,一些专家认为顺风车的价格应该限定在巡游出租车价格50%的范围内,“有一个最高的标准,不高于巡游出租车运价的50%,是不是更低可以再讨论。因为出租车是营运的,一次出行,这是一个营运价,合乘的时候,我是跟你合的,我只分摊一半,分摊一半是这一半的营运价,而不是成本价,所以最高价格不超过50%”,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陈越峰表示。
对于这一限价的幅度,一些专家持有异议,核心的问题在于到底哪些成本是可以进行“分摊”的,哪些成本不应该进行分摊。在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总督导张柱庭看来,分摊的项目是一定的,至少不能包括劳务费,“有没有驾驶员劳务费是和出租车的分水岭,收劳务费就是出租车了”,张柱庭表示,而这也意味着巡游车50%的限价仍旧过高――其中包含了对劳务费的折算。
被普遍讨论的问题还包括顺风车行为是否应该设有次数限制,以及顺风车行为的达成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次数限制的问题上,会议达成的普遍观点是应该进行次数限制,这种限制被认为可以帮助明确顺风车的非运营性质,但是对于具体的限制次数上尚存在讨论空间――在一些地方的规定中,每位车主每日顺风车的单数被限定为2次或者4次;在顺风车行为达成上,普遍认为应该是车主先进发布合乘信息,而不是乘客先发布出行需求。
这些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排除掉顺风车内的运营行为,在此前的一段时间中,在出行平台中,顺风车出现了大量的运营行为,并由此引发了诸多安全事件――2018年发生的两起顺风车安全事件车主事后被证明实际上存在运营动机。
实际上,商业公司的参与一方面让顺风车业务得以扩大的同时,也让增加了顺风车这一行为的复杂程度,其核心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认定平台在顺风车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责任。
“顺风车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个人发起的顺风行为,还有一种是平台组织的顺风行为,前者由双方按照合同约定或口头的约定,来实现风险的共担;后者既然是平台行为,不管平台是否获利,都应该尽到安全防范的责任,但不管哪种情况,个人该遵循契约的精神。”,中国交通报副总编辑陈林表示。
刘汝忠认为,平台的责任可以参考《电子商务法》中的相关条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顺风车平台所收取费用的形式――即是按信息撮合收取固定的居间服务费还是按照交易额进行抽成――来区别对待其责任,对于此,张柱庭认为平台公司依然是企业,所有的公共安全责任,安全生产责任,以及信息安全责任,都是其底线,必须遵守的,不应该在这方面打折扣。
所有的规范都需要监管层的进一步动作进行加强,然而,针对顺风车这一行为,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即使是2018年对于各个出行平台入驻式的监管,监管主体也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检查组。
顺风车行为以及为其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交通运输行业?在这一点上,会议出现了一些分歧,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晖表示按照顺风车的产业特征来看,它应该是属于信息业而非交通业;对于这一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提出了不同观点,程世东认为顺风车的线下还是一种公益行为,线上只是提供信息撮合,是实现行为的一种手段,纳入信息业里边,并不是是特别妥当。在程世东看来,顺风车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因此也就并非一个行业。
这种分歧的解决尚需要更高层面的法规明确,在陈晖看来,目前对于顺风车的规范,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顺风车需要在国务院层面来制定一个行政法规,只有交通部门来制定部门规章,我觉得那个效果会大打折扣”,陈晖表示。
注:文/宋笛,出处:投中网,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邦动力网立场。